废除死刑的理论依据
——为什么张扣扣案与章莹颖案判决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为什么张扣扣案与章莹颖案判决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琚新国律师 2019-7-21
最近有两个故意杀人案相继判决,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一个是张扣扣故意杀人案,中国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个是章莹颖在美国被杀案,美国法院判决杀人犯终身监禁,逃过一死。
以国人的观点来看,那个杀害章莹颖的杀人犯似乎更应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个张扣扣为母复仇案似乎更应该被饶过一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与国人观念倒置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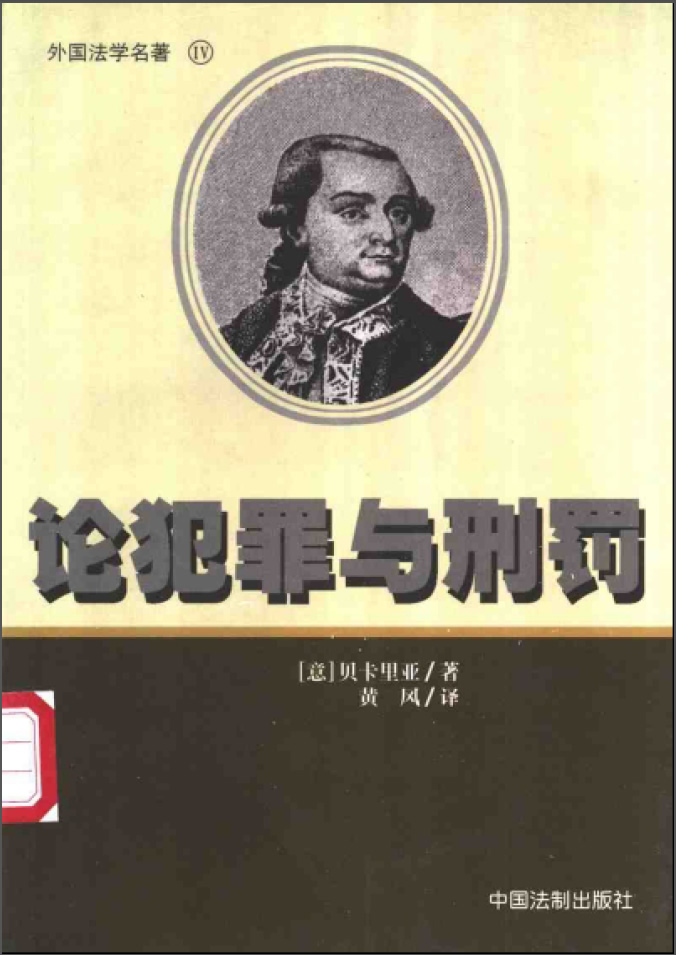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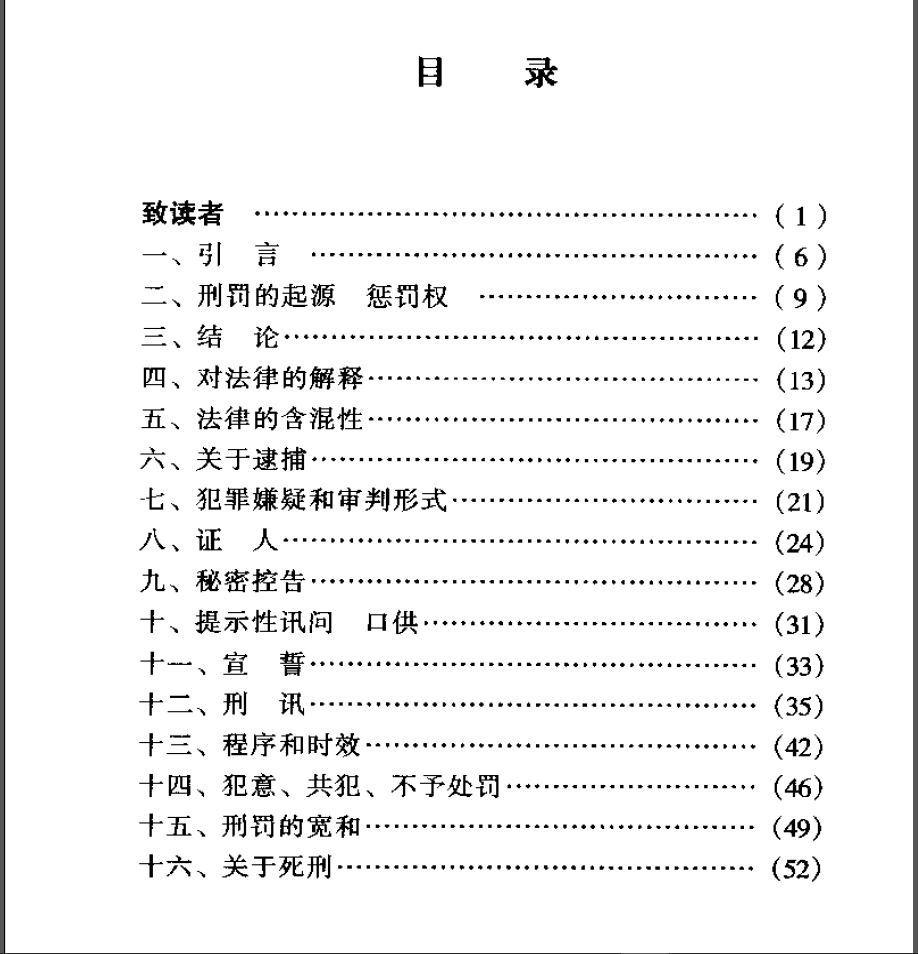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美国社会在对待死刑的问题上秉持的观念。正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西方人重视人权,所以在死刑问题上十分谨慎,更有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美国虽然没有完全废除死刑,但践中已经很少判处死刑,就算判了死刑,也很少立即执行。他们的理论源头就是1764年首次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当时欧洲的刑事司法制度黑暗、残酷、野蛮,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写作了这本《论犯罪与刑罚》,以批判当时的刑事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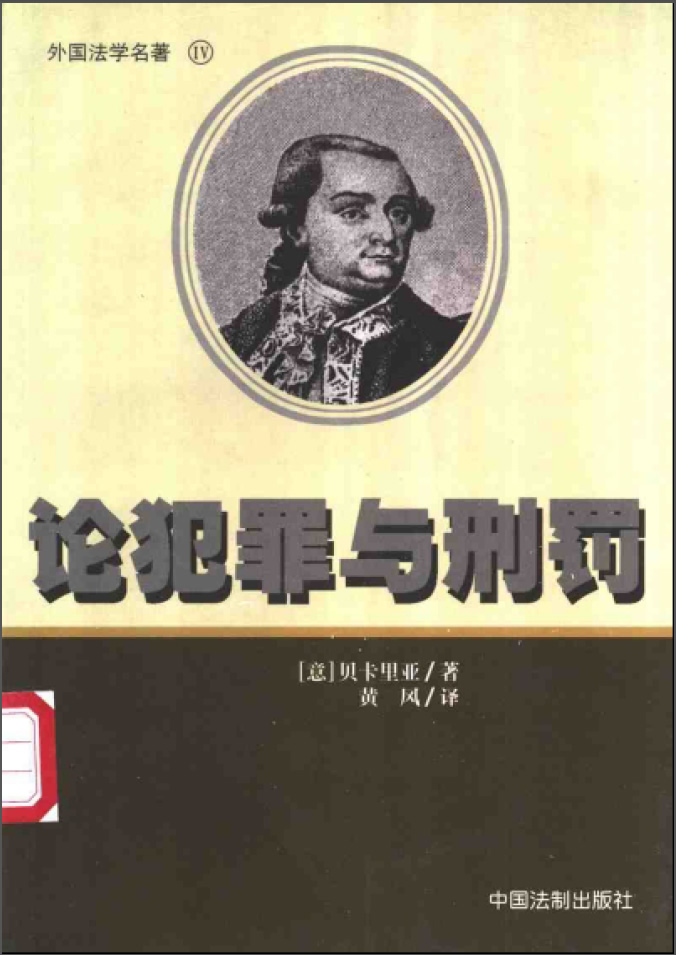
这本书出版后,震动了欧洲,后来,不少欧洲国家纷纷废除包括死刑在内的酷刑。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社会上层主要是欧洲移民,而且主要是法律专家。美国从建国一开始,就移植了欧洲的法律思想。所以在对待死刑的态度方面,与欧洲是一致的。
《论犯罪与刑罚》的第十六章,讨论了死刑。笔者尽量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把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纳描述为以下五点:
一、死刑起不到让罪犯回心转意的作用。死刑犯之所以能成为死刑犯,是因为他们在实施犯罪前就已经不怕死了。
二、想用死刑来震慑那些即将实施犯罪的人,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实施犯罪,那么,他们仍将实施,他们并将会做好赴死的准备。
三、想用死刑来震慑和教育社会上的公众,是没有用的。因为临场观刑的人看到刽子手行刑时,内心的主要反映是对死刑犯的同情,和对刽子手的鄙视。结果反而冲淡人们对犯罪的憎恶。
四、执行死刑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过后,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渐渐淡忘。从而磨灭了案件对社会的教育意义。而判处终身监禁,能让这个罪犯终生成为活生生的教材。
五、统治者没有废除死刑,不是因为统治者不想废除,而是因为“杀人偿命”的古老观念仍旧在民众的头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统治者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以下摘录《论犯罪与刑罚》的第十六章译文原文,供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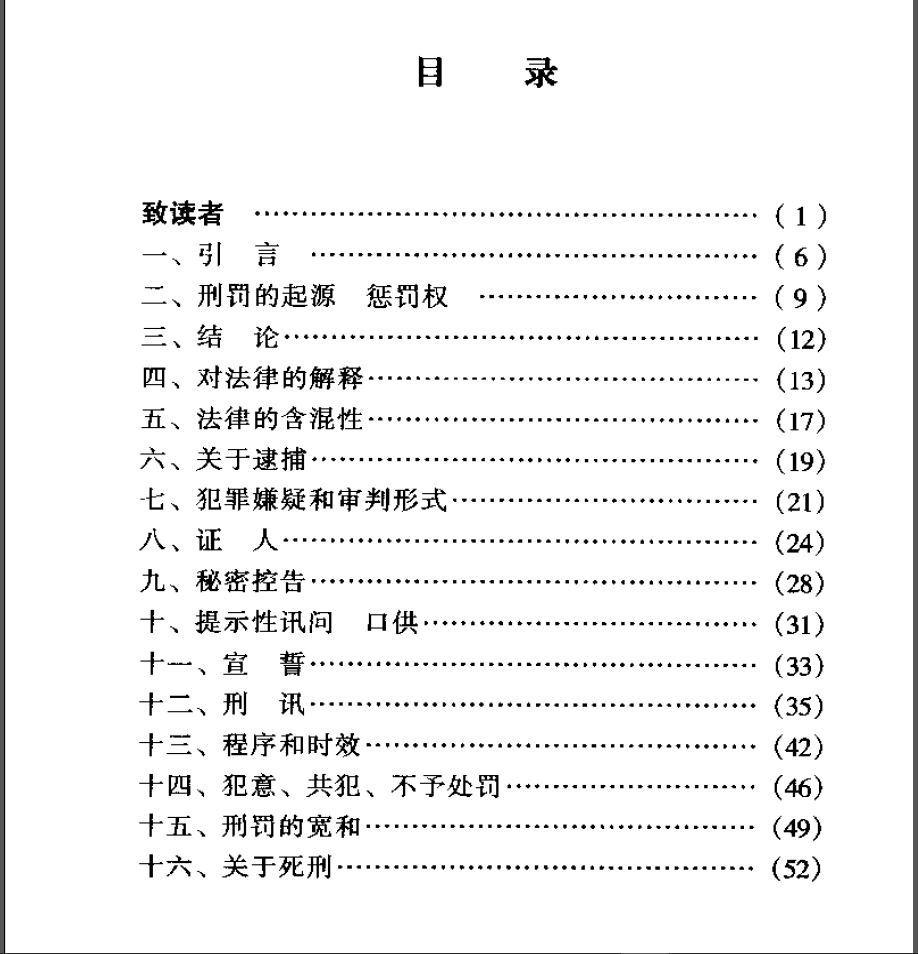
十六、关于死刑
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
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
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这当然不是造就君权和法律的那种权利。君权和法律,它们仅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总和,它们代表的是作为个人利益结合体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操使呢?每个人在对自己做出最小牺牲时,怎么会把冠于一切财富之首的生命也搭进去呢?如果说这己成为事实的话, 它同人无权自杀的原则怎么协调呢?要是他可以把这种权利交给他人或者交给整个社会,他岂不本来就应该有这种权利吗?
因而,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我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
只有根据两个理由,才可以把处死一个公民看做是必要的。第一个理由: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确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他的存在可能会在既定的政府体制中引起危险的动乱。再者,当一个国家正在恢复自由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由已经消失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时候,这时混乱取代了法律,因而处死某些公民就变得必要了。如果一个举国拥戴的政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拥有力量和比力量更有效的舆论作保护,如果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只是真正的君主,财富买来的只是享受而不是权势,那么,我看不出这个安宁的法律王国有什么必要去消灭一个公民,除非处死他是预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 这是死刑据以被视为正义和必要刑罚的第二个理由。
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们回心转意。莫斯科的伊丽莎白女皇统治的20年,为人民的父母官们树立了杰出的典范,同祖国的儿子们用鲜血换来的无数成果相比,这一典范毫不逊色。如果几百年的历史、这20年的统治和罗马公民的范例都说服不了那些怀疑理性语言、倾服权威语言的人,那么,考察一下人的本性,就足以听到我的主张的真谛。
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确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习惯是一种主宰着一切感知物的王权,一个人说话、走路、寻求生活需要,都离不开习惯的帮助;同样,道德观念只有通过持续和反复影响才会印入人的脑海。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时的,如果把罪犯变成劳役犯,让他用自己的劳苦来补偿他所侵犯的社会,那么,这种丧失自由的鉴戒则是长久的和痛苦的,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种行之有效的约束经常提醒我们:如果我犯了这样的罪恶,也将陷入这漫长的苦难之中。因而,同人们总感到扑朔迷离的死亡观念相比,它(劳役)更具有力量。
欲望促成人健忘,即便对于一些最紧要的事物,这种健忘也是自然而然的,死刑所给予的印象是取代不了它的。一般规律是:狂暴的欲望只能暂时地攫取人心,而不能持续下去,它适合于像波斯人或古代斯巴达人那样去搞革命;然而,在一个自由而安宁的政府领导下, 印象与其说应该是强烈的,不如说应该是经常的。
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已变或了一场表演,而且,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占据观众思想的,主要是这两种感情,而不是法律所希望唤起的那种健康的畏惧感。然而,有节制和持续的刑罚则使这种畏惧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为这种感情是唯一的。刑场与其说是为罪犯开设的,不如说是为观众开设的,当怜悯感开始在观众中超越了其他情感时,立法者似乎就应当对刑罚的强度做出限制。
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没有哪个人经过权衡之后还会选择那条使自己彻底地、永久地丧失自由的道路,不管犯罪能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因而,取代死刑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决意的心灵。
另外,很多人以一种安详而坚定的表情对待死刑。其中,一些人是出于狂热,一些人是出于几乎一直伴随他走入坟墓的空虚,另一些人则是出于一种最后的绝望的试图:或者生存下去,或者忍受不幸。但是,在桎梏的束缚中,在棍棒的奴役下,既没有狂热,也没有空虚,绝望也结束不了他所吞食的恶果,而是使他开始尝受这些恶果。
我们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极端的但短暂的痛苦,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消磨,忍耐不住缠绵的烦恼,因为,它可以暂时地自我收缩以抗拒暴力和短暂的痛苦。然而,这种强烈的伸缩性却不足以抗拒时间与烦恼的长期和反复的影响。
每次以死刑为国家树立鉴戒都需要一次犯罪,可是,有了终身苦役刑,只一次犯罪就为国家提供无数常存存的鉴戒。如果说重要的是经常向人们显示法律的力量的话,死刑的适用就不应是间隔很长的,因而,就要求犯罪经常发生。这样,为了变得有用,死刑就必然要改变本来应该给予人们的那种印象,这就意味着它要想是有用的,就应当同时是无用的。
有人说,终身苦役同死刑一样也是痛苦的,所以,它也同样是残酷的。我认为:如果把苦役的受苦时间加在一起,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些苦难是平均分配于人的整个生活,而死刑却把它的力量集中于一时。苦役这种刑罚有一个好处,它使旁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畏惧,因为,前者考虑的是受若时间的总和,后者则分心于眼前的不幸而看不到将来。在前者的想象中,刑罚的恶果变的昭彰了,而后者却从他那麻木不仁的心灵中汲取旁观者所无法体验和理解的安慰。
我知道,发展自己的内心情感是一门依靠教育才能学到的艺术。然而,不能因为盗贼不能很好的解释自己的行为原则,就说这些原则不怎么起作用。瞧,很快我们就会看到那些只有绞刑或轮刑才能阻止其犯罪的盗贼和杀人犯所进行的推论了:
“我应该遵守的算是什么法律呀!它在我和富人之间设置了一道鸿沟。富人对我一毛不拔,反倒找借口让我偿受他所没尝受过的痛苦。这是谁定的法律?是富人和权势者。他们对于穷人阴陋的茅舍从来不屑一顾,他们眼看着儿童们在饥饿中哭嚎,妇女们在伤心落泪,却连一块发了霉了面包也不肯拿出来。我们要斩断这些给多数人造成灾难并为少数懒惰的暴君服务的绳索!我们要向这不平等的根源开战!我将重新恢复自然的独立状态,我将以自己的勇敢和辛勤来获取一定时间的自由愉快的生活。也许痛苦和忏悔的一天会来临,但那是短暂的,在度过多年自由和享乐的生活之后,我会有那么一个烦恼之日。作为少数人之王,我将纠正命运的荒谬,将让那些暴君在被他们的奢侈侮辱得还不如他们的马和狗的人面前,面如土色,失魂落魄。”就这样,一种信念充斥于那些忘乎所以的罪犯的头脑,教给他去做一种简单的忏悔,并告诉他长时间的幸福是完全可能的。因而,大减少了他对悲惨结局的恐惧。
但是,一个人如果发现他将在生活于自由之中的本国公民的眼皮底下,在苦役和痛苦之中,度过许多岁月甚至是整整一生,成为曾经保护过他的法律的奴隶,那么,他将把这种结局同成败未卜的犯罪、同他可能享受到的暂时犯罪成果进行有益的比较。那些现在看来是因鼠目寸光而葬送了自己的教训所给予他的印象,比一种酷刑的场面要强烈的多。酷刑的场面给予人们的常常是一副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
用死刑来向人们证明法律的严竣是没有益处的。如果说,欲望和战争的要求纵容人类流血的话,那么,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约束者,看来不应该去扩大这种残暴的事例。随着人们用专门的研究如手续使越来越多的死亡合法化,这种事例就更加有害了。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去杀掉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现象。
真正的和最有益的法律是怎样的呢?那就是当一向到处声张的私人利益不再喧嚣或者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时,所有人都情愿遵守法律。人们对死刑怀有何种感情呢?我们从每个人对刽子手所采取的仇视和鄙夷的态度中就能看到这种感情。然而,这位刽子手也是公共意志的无辜执行者,是一位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善良公民,同那些对外作战的无畏战士一样,他也是对内治安的必要工具。那么,这一矛盾的根源何在呢?为什么人们的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致压倒了理性呢?因为,人们在心灵的最深处,在那个比其他任何部位都更多地保留着古老自然的原始状态的地方,总认为:自己的生命不受任何用其铁腕统治世界的人的支配,除非出现这种必要性。
聪明的司法官员和严厉的执法牧师泰然自若地用缓慢的仪式把犯人慢慢带向死亡,不幸者在痛苦的抽搐中等待着最后的致命一击,而法官却熟视无睹、漠然置之,或许还暗暗地对自己的权威感到得意,品味着生活的惬意和乐趣。人们看到这种情景会怎么想呢?他们将叹道:“咳,这些法律只不过是施加暴力的借口,煞费苦心、残酷横暴的司法手续只不过是为了更稳妥地把我们当作牺牲品,奉祀给贪得无厌的暴政偶像而订立的协约用语罢了。杀人被说成是一种可怕的滔天大罪,我们却看到有人心安理得地实施它。这一事例使我们受益匪浅。过去,我们根据一些描述,把暴力致死看作一种可怕的场面,然而,现在我们却把它看做是一瞬间的事情。对于那些并不等待死亡,因而几乎尝不到死刑痛苦的人来说,这种事情就更不算什么了。”这些就是那些打算犯罪的人清醒地或者恍惚地做出的危险而有害的推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对他们更起作用的不是信仰本身,而是信仰的滥用。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对某些犯罪施用死刑己成为几乎所有世纪和国家的惯例,那么,我将答道:在不受时效约束的真理面前,这称惯例正在消泯。人类历史给我们的印象是:谬误好似无边的烟海,在这之上,漂浮着稀少的、混杂的、彼此远离的真理。用人作牺牲品是几乎所有国家的共同习惯,而谁敢因此而为这个习惯辩解呢?有少数一些社会,仅仅在短暂的时期内摒弃了死刑,这并不是对我的观点的否定而是一种支持,因为这正符合伟大真理的命运。同笼罩着人类的漫长黑夜相比,这些真理的出现只不过是一次闪电。幸运的时代日前仍未到来,一旦这一时代来临,真理将像今天的谬误那样为大多数人所掌握。至今只有神明所揭示并将其单独分离出来的那些真理才不受这项普遍规律的支配。
同信守蒙昧习惯的众人发出的喧嚣相比,一个哲学家的呼声确实太微弱了。 然而,那些分散在大地上的少数明智者,将在内心深处向我发出共鸣。 如果说,真理可以逾越硬把它同君主隔开的重重障碍而登上王位的话,那么,它懂得,正是这些明智者的秘密赞助才使它获得成功。 它还知道:征服者的血腥名声将对这座王位不起作用,而公正的后代将让它在泰塔斯、安东尼和图拉真的和平战利品中占据首位。
倡导和平的美德,倡导科学和艺术的君主是人民的父亲,是加冕的公民,他们权力的增加就是臣民的幸福,因为,他们的权力削弱了那些因不可靠而变得残酷的专制中介(帮凶)。我们看到这些君主正坐在欧洲的一些王位上,如果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他们颁布的,人类该多么幸福啊!人民的真诚愿望如能上达君主,往往是一种吉祥,而那些专制的中介(帮凶)却将它们扼杀。这些君主之所以让一些古老的法律继续存在,是因为从谬误身上剥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人尊敬的锈衣的确非常困难。而明智的公民正是因此才主张以更大的热情继续提高这些君主的权威。
(完)
郑州律师:琚新国律师
执业机构: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豫博大厦(东塔)17、18、19楼。
咨询电话:13673383391。
豫ICP备2023000064号-1
执业机构: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豫博大厦(东塔)17、18、19楼。
咨询电话:13673383391。
豫ICP备2023000064号-1

扫一扫 微信咨询